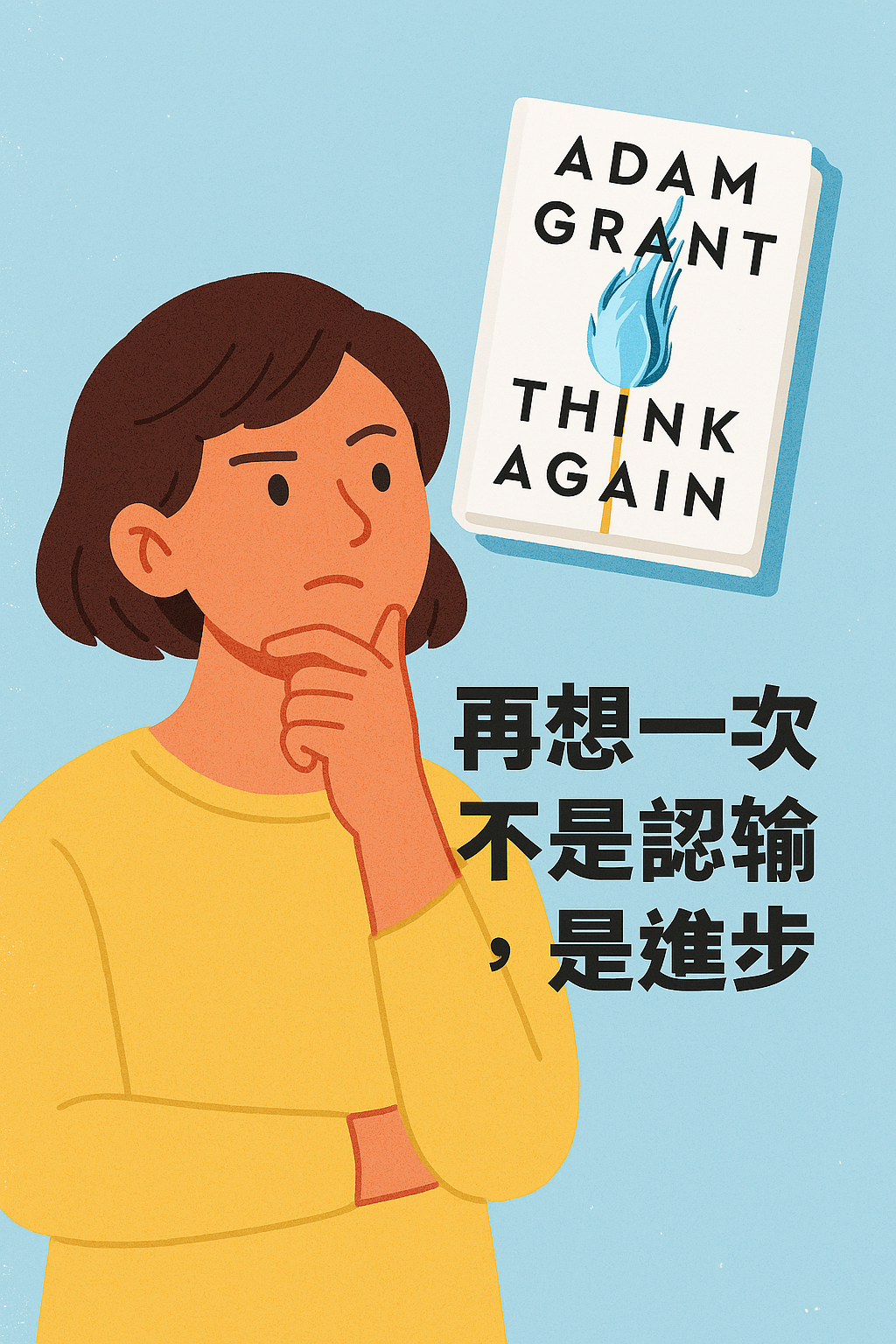
再想一次不是認輸,是進步:Adam Grant《逆思維》讀後反思與延伸
2025 Feb 19 行銷
《逆思維》:再想一次,是一種能力,也是勇氣
寫給那些太努力,也太用力證明自己沒錯的人
我們總以為,只要夠努力、夠理性、證據列得夠完整,就能說服對方、突破現況。
但亞當.格蘭特(Adam Grant)在《逆思維》(Think Again)裡提出一個不太舒服的提醒:
「你最堅持的東西,有時正是你無法突破的原因。」
這不是要我們變得搖擺,而是提醒我們:沒有持續修正的信念,不是真正有力的信念。
這篇不是書摘,而是我在閱讀過程中,慢慢被敲醒後整理出來的幾個主軸與提問。
如果你正在卡住、想改變卻不確定該改哪裡,這篇是寫給你,也寫給我自己的。
(故事一)
懷疑自己的人,反而更有可能成功
2008 年冰島金融風暴,國營銀行私有化失控,國家幾乎破產。當時的總理大衛.奧德森,是這場災難的推手之一。
他沒有經濟專業背景,卻堅信過去的治理經驗就夠了。即使即將卸任後擔任央行理事、連續判斷錯誤,他仍拒絕承擔責任。
幾年後,他再度參選,認為自己的經驗正是冰島需要的。
但那一年,也有另一位候選人:哈拉.托馬斯多蒂爾。
她沒政黨支持,民調不到 1%。一開始,她甚至不覺得自己夠格當總理。
但她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對才參選,而是因為她無法接受「那個應該為災難負責的人」繼續主導未來。
她主動回應公眾問題、不躲避討論、不進入口水戰。 最後,她紅上央視,遠遠超越奧德森。
葛蘭特說:
「冒牌者症候群不一定是弱點,有時反而是推動者。」
懷疑自己的人,更常聆聽、更願意調整、更認真學習。這讓他們在面對未知時,擁有更高的彈性與效能。
📌 我給自己的練習:
我最近做的哪個決定,是因為「我之前就這麼說了」?
那真的還是對的選擇嗎,還是只是不想改變?
(故事二)
說服的起點,是讓對方說完
在疫苗爭議最激烈的時期,有一組醫療倡議者試圖改變部分家長對疫苗的極端排斥。他們的做法讓人耳目一新。
這群「疫苗溝通師」在與家長對話時,並不急著灌輸正確知識。他們先讓對方完整地表達擔憂,從頭到尾聽完。然後說:
「我理解你的顧慮,那些真的很合理。我自己也會擔心。只是剛好我也看到一些資料,也許可以讓你參考看看。」
沒有高壓,沒有辯論,只有共感與補充。結果如何?
原本堅決不讓孩子打疫苗的家長,有將近 10% 在一次對話之後就改變了態度。
這不只是說服技巧,更是一種「給人再思考空間」的心法。
📌 我給自己的練習:
我上次是什麼時候,真的讓一個人完整說完他的顧慮,而不是急著反駁?
多說還是少說,取決於你想創造什麼空間
疫苗故事讓我重新認識「說服」這件事。
我們以為有效的說服是把證據說滿、把對錯講清,但真正打動人的,是讓人保有思考與選擇的餘裕。
這讓我開始思考:什麼時候該說多一點,什麼時候該說少一點?
在「建立理解」的時候,講多一點沒關係。 如果你在寫文章、製作教材、做演講,越能呈現觀點的多元,越容易打開聽者的腦袋。
但在「讓人改變」的時候,重點不是你講得多清楚,而是對方有沒有感覺安全。
你讓他說完話、接住他、提供一點點資訊,他自己會補上後面那一大段。
這兩種情境的策略雖不同,但邏輯一致:
讓人可以不防衛地接近「可能性」。
所以你該多說還是少說,不是看你有沒有材料,而是看——你是想證明自己,還是想讓對方有機會再想一次?
📌 我給自己的練習:
我是不是有點太習慣講滿所有細節,只是因為我想證明自己是對的?
四種思維角色:你是哪一種?
葛蘭特在書中提出了四種我們常陷入的思維模式:
- 檢察官:專注於指出他人的錯誤,把對錯當成勝負
- 政治人物:根據支持者立場調整自己觀點,迎合多於誠實
- 傳教士:堅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,說服他人成為唯一目標
- 科學家:提出假設,驗證後修正觀點,願意讓證據挑戰自己
他認為,只有「科學家思維」能夠長出真正的逆思維能力。
📌 我給自己的練習:
我在日常對話中,是習慣捍衛觀點、爭輸贏?還是願意說「也許我錯了」?
我對這四種分類的補充
我認同葛蘭特的分類方式簡潔有力。但在現實中,角色之間的界線常常是模糊的。
有些人外表是傳教士,內在其實是政治人物;有些人看似檢察官,其實只是缺乏安全感的懷疑者。
所以我更關心的是:「這個人內在是否有能力在不被否定的前提下接受挑戰?」
也就是說,安全感 × 衝突容忍力,決定了我們是否能成為真正的思考者。
這樣看來,科學家思維不只是願意修正自己,更是在建構一種「能讓自己和他人都不怕錯」的環境。
最後的練習:再想一次,不是否定自己,而是進步的開端
再想一次,不代表你錯了,而是你願意承認:「我不會一次就對。」
對我來說,這不是一種謙卑,而是一種訓練。
我試著問自己:
- 我願不願意讓一個人說完他的話,即使我早就不認同?
- 我願不願意讓團隊成員挑戰我,而不覺得丟臉?
- 我願不願意說出「我還沒想清楚,但我想聽聽看」?
📌 我給自己的練習:
下一次我覺得「自己很確定」的時候,能不能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空間,說—— 「也許還有別的可能,也許我還可以再想一次。」

